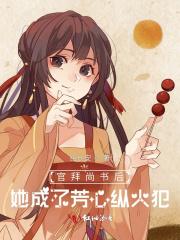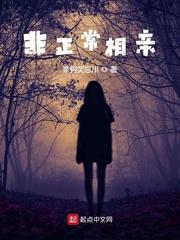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我是县城婆罗门 > 第375章 财富金币被叫停(第3页)
第375章 财富金币被叫停(第3页)
她播放了平措的录音。
静默片刻,扎西低声说:“我也有句话,一直没对我说阿妈讲。”
他掏出手机,按下录音键。
“阿妈……我知道你怪我把弟弟送进军营,后来牺牲了。可我当时真的以为,那是条好出路。对不起……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是英雄。我只是……想你抱我一次,像小时候那样。”
他说完,把头埋进膝盖。
另一个技术员小杨也开口了:“我爸走的时候我才十岁。他肺癌晚期,疼得整夜呻吟。我一直躲在外面不敢进去。直到现在,我都不敢一个人去医院。我想告诉他:爸爸,我不是不怕你,我是太怕失去你了。”
泪水无声滑落。
沈安安没有阻止这场倾诉。她知道,在这片被神灵注视的土地上,有些伤口只有说出来,才能真正愈合。
她最后打开自己的录音设备,轻声道:
“李老师,如果您还能听见……我想告诉您,我没有辜负您的信任。赵强的声音,已经被一百二十三个人听过。有人因此给失联多年的兄弟打了电话;有人听完后回家抱住父母哭了一整晚;还有一个孩子,把他录进了作文里,题目叫《我听见了光》。”
她顿了顿,声音微颤:“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您坚持要把那段录音交给我。因为有些声音,不只是声音。它们是钥匙,能打开我们心底最深的门。”
那一夜,暴风雪咆哮不止,而小小气象站内,却流淌着前所未有的宁静。
次日清晨,雪停了。阳光洒在银白大地上,美得令人窒息。
他们将平措与德吉的信件副本留在气象站桌上,附上一张纸条:“致未来的发现者:有些爱情从未被见证,但它们真实存在过。”
离开前,沈安安在门外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刻着两行字:
>“此处曾有两人以信传心,以声取暖。
>若你路过,请轻声说话。”
车队再次启程。
随着深入羌塘腹地,移动驿站的影响悄然扩散。牧民们开始自发传递消息:哪个营地来了“会说话的车”,哪个老人录下了遗言,哪个孩子听了祖母的歌声后第一次开口叫“阿妈”。
第五站,一位失语多年的自闭症少年,在听到母亲哼唱童年儿歌的震感反馈后,突然伸手握住她的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又指了指天空。
翻译含泪解释:“他说,心和星星,都在跳。”
第六站,一对因误会分离三十年的恋人重逢。男方已是独居老人,女方则守寡多年。他们在录音舱里相对而坐,谁也没先开口。最后,是沈安安提议:“不如各自录一段话,不给对方听,只交给时间。”
一个月后,她在回访数据中发现,两人竟不约而同录下了同一句话:
“如果还能重来,我想早点牵你的手。”
她将这两段音频合并成一首双声部音频诗,命名为《迟到的情书》,收入“微光档案馆”永久收藏。
然而,并非所有故事都有温暖结局。
第七站,一名年轻母亲执意要为夭折婴儿录音。她说孩子从未说过一句话,但她坚信“他一定想告诉我什么”。
沈安安犹豫再三,最终同意使用AI情感补全模型,基于母亲哺乳时的语调、摇篮动作频率、睡眠呼吸节奏,生成一段“假设性回应”。
结果出乎意料??当那段柔和童音响起:“阿妈,我不疼了,那里有很多光,还有小羊陪我玩……”女人当场崩溃,继而狂喜,反复播放数十遍,甚至拒绝关闭设备。
沈安安紧急介入,暂停服务,并召开内部会议。
“我们越界了。”她说,“哪怕初衷是善意,也不能替一个从未发声的生命‘代言’。那是对生命的亵渎。”
她下令彻底删除该模型在儿童领域的应用权限,并在系统后台增设“生命阶段识别锁”:凡涉及未成年人或无语言能力者,禁止任何形式的语音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