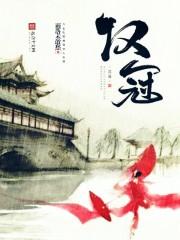笔趣阁>贫道要考大学 > 第185章 挺舒服的吧班长6K大章为白银盟云尘夏天加更(第1页)
第185章 挺舒服的吧班长6K大章为白银盟云尘夏天加更(第1页)
庄老师一脸狐疑地下楼丢垃圾去了。
林梦秋带着陈拾安继续往前走,直到在房号406的门前停下。
她拿出一串钥匙,找出贴着小标签纸的那枚,插进了钥匙孔里。
陈拾安抬眼看着面前的宿舍门,比起。。。
暴雨过后,山间清晨格外清透。陈拾安推开木窗,湿漉漉的雾气裹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远处梯田如镜,倒映着初升的太阳,像一片片碎金浮在半山腰。他深吸一口气,将昨夜那封VK-002的留言截图保存进《听心录》新增章节??《光的传递者》。
桌角的老式录音机静静立着,磁带已换成了空白新带。这是小禾寄来的,随信附了一张纸条:“老师,我想开始说新的故事了。”他轻轻按下“录制”键,却没说话,只是让机器空转。沙沙的走带声像心跳,像呼吸,像无数未曾启齿的心事正缓缓苏醒。
手机震动,是温知夏发来的会议通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拟召开“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创新试点项目评审会”,邀请“少年声库”团队作为唯一民间代表汇报工作。附件中列有严苛要求:需提交三年运营数据、伦理审查报告、危机干预案例脱敏分析,以及一项核心议题??**如何界定“倾听”的边界?当情感支持滑向心理治疗,谁来负责?**
她补了一句:“他们想把‘同声共振’纳入体制,但前提是??你要交出控制权。”
陈拾安盯着屏幕良久,没有回复。他知道,这是一次真正的十字路口。接受,意味着资源、合法性与更广的覆盖;拒绝,则可能被边缘化,甚至面临监管收紧。但他更清楚,一旦“少年声库”变成官僚系统中的一个KPI指标,那些深夜里颤抖的声音,或许就会沦为报表上的冰冷数字。
他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泛黄的手册??那是最初设计“夜语亭”时写的《倾听守则草案》。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不替人做决定,只陪人走过决定前的黑暗。”他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曾被自己用红笔写下一句话:“若有一天我们开始教孩子该怎么活,那就已经背叛了初衷。”
窗外传来脚步声,林晓雨背着双肩包走了进来,头发微湿,像是刚从山道跑上来。“老师,我昨晚做了个梦。”她坐到桌边,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什么,“梦见我又站在舞台上,台下全是评委,他们举着分数牌,上面写的是‘情绪价值贡献度’‘倾诉转化率’‘治愈指数’……我说不出话,喉咙像被缝住了。”
陈拾安沉默片刻,倒了杯热茶递给她。“这不是梦,是预警。”他说,“有人正试图把‘听见’变成一门可以打分的考试。”
林晓雨低头摩挲茶杯边缘:“可如果我们不参与规则制定,别人就会替我们定。我已经联系了五位‘同声共振’志愿者,都是亲历者,愿意一起去北京作证??不是作为数据,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
他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曾经躲在耳机后不敢抬头的女孩,如今眼神坚定得像山脊。
“好。”他终于开口,“但我们不去讲模式、谈技术、秀成果。我们就带一盘磁带去。”
“磁带?”
“对。里面录了过去三个月里,最普通也最真实的三十段对话。没有戏剧性,没有逆袭,只有一个人说‘我今天又迟到了’,另一个人回‘嗯,我在’;一个孩子说‘我觉得活着好累’,另一个说‘那你先歇会儿,我陪你’。”
“就这样?”
“就这样。”他笑了笑,“让他们听听,什么叫真正的‘在场’。”
三天后,北京。
评审会议室肃穆庄严,长桌两侧坐着来自教育、卫健、公安系统的十余位专家。投影仪亮起,PPT模板统一为蓝底白字,标题写着《“少年声库”项目阶段性评估报告》。轮到陈拾安发言时,他没有打开电脑,而是从帆布包里取出一台老式便携录音机,放在会议桌上。
全场静默。
“各位领导、专家,我没有PPT。”他说,“但我有一段声音,想请大家听一听。”
他按下播放键。
第一段录音响起??
>“喂?是你吗?”
>“是我。你哭了吗?”
>“没有……就是眼睛进沙子了。”
>“哦。那我等你说完再挂。”
>(长久的沉默,只有轻微抽泣)
>“其实……我昨天摔了饭碗,我妈骂我是废物。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手抖……每次紧张都会这样。”
>“我知道。我弟弟也这样,医生说是焦虑症。你不废物,你是累了。”
>“真的吗?”
>“真的。你要不要听个笑话?我上次把自己锁在厕所哭,结果手机没电,还得求妹妹帮我开门。她说:姐,你要是真想躲,至少带充电宝啊。”
>(轻笑,继而啜泣)
>“谢谢你……我能再打给你吗?”
>“能。我一直都在。”
录音结束,会议室鸦雀无声。
第二段接续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