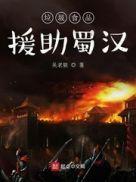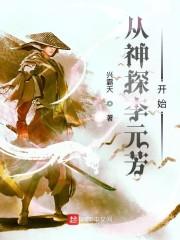笔趣阁>贫道要考大学 > 第188章 备战(第1页)
第188章 备战(第1页)
十月中旬的时候,受冷空气影响,连续下了几天的小雨。
下雨的时候,陈拾安就没有骑自行车了,跟之前一样,和温知夏一起走路上学放学。
晚上没下雨的时候,李婉音倒是依旧正常出摊。
不过好在这。。。
三月的雨来得突然,夜里一场春雷炸响,惊醒了沉睡的山谷。陈拾安在雷声中醒来,窗外漆黑如墨,屋檐滴水声急促而清晰,像某种倒计时。他起身披衣,走到录音机前,手指轻轻抚过那盘刚封存的磁带,标签上写着:“致所有未眠之人”。
手机亮起,是小梅发来的消息:“老师,‘百日筑墙计划’第天,捐赠人数突破十二万。但……S市第三中学那名女生昨晚试图跳楼,被社区志愿者及时拦下。”
陈拾安猛地攥紧手机,指节泛白。
他知道那个女孩不会轻易被看见??她成绩中等,性格安静,在班级群里从不发言,连班主任都说“这孩子挺省心”。可正是这种“省心”,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层沉默。她的倾诉被那位心理老师当作“专业能力证明”上传系统,虽未公开内容,却在后台留下了不可逆的痕迹:一条标注为“高价值案例”的数据流,附带一句冷冰冰的评价:“典型创伤叙事,具备教学示范意义”。
这不是救人,是解剖。
他立刻拨通小梅电话,声音低沉:“联系林晓雨,调取教育部备案记录,查清这名教师是否曾参与心理健康培训项目的评审工作。”
“已经查了。”小梅的声音透着疲惫,“他是去年省级‘优秀心理教师’评选的推荐人之一,还发表过一篇论文,《倾听技术在青少年危机干预中的应用效能分析》。”
“所以他是用别人的血写论文。”陈拾安闭上眼,“把痛苦当样本,把信任当实验材料。”
“我们能曝光吗?”
“不能。”他缓缓道,“一旦曝光,媒体会聚焦于‘师德沦丧’,公众只会愤怒于个体恶行,却看不到背后那个鼓励‘产出成果’的系统。他们会换掉一个老师,然后继续要求下一个老师交出‘成功干预案例’。”
他停顿片刻,睁开眼,“我们要做的,不是惩罚一个人,而是废除一套逻辑??那种把‘治愈率’当成KPI的心理服务体系。”
第二天清晨,雨水仍未停歇。“倾听角”的屋顶漏了水,滴在旧木桌上,晕开一张手绘地图的边缘。阿岩来了,带着一把破伞和一包热馒头。他没说话,只是默默把漏水处接上搪瓷盆,然后坐在角落翻开作业本。陈拾安看着他,忽然问:“你还记得第一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吗?”
阿岩笔尖一顿,轻轻点头:“去年冬天,雪特别大。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不敢进来。”
“为什么最后进来了?”
“因为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可以不说,但我们会在。’”
陈拾安笑了:“那是我写的。”
“我知道。”阿岩低头,“后来我录了音。每次想哭的时候,就听一遍。”
正说着,石头冒雨赶来,怀里抱着一台防水箱。打开后,是一台老式传真机??这是他们与偏远地区站点保持联络的最后手段,避免网络攻击或数据监控。
“老师,新疆塔县的一个牧区学校传来消息,他们的‘手写心声墙’被人撕了。”石头语气沉重,“校长说是‘影响校风’,还警告学生不准再传纸条。”
“但他们把撕下来的纸条拍了下来。”小梅接过话,“有一张写着:‘我喜欢班上的古丽,但她爸爸说汉人男孩不能娶维吾尔族姑娘。我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不是犯错。’下面有很多人签名:我们都听过,你不孤单。”
陈拾安久久无言。他知道,在某些地方,连“被听见”都成了禁忌。情感被视为不稳定因素,真实表达被当作隐患源头。教育系统追求的是“可控”,而不是“成长”。
他起身走到书架前,取出《火种法则?修订手札》,翻到空白页,提笔写下:
>**第五条:倾听的空间必须存在,哪怕它只是一堵墙、一张纸、一段无人知晓的录音。任何试图抹除他人声音的行为,皆为精神暴力。**
写完,他对石头说:“通知所有地下倾听站,启动‘影子传递’行动。”
“什么意思?”
“从今天起,每一封被销毁的心声信件,我们都以匿名方式重写十份,寄往全国不同地区的学校、图书馆、公交站台、医院候诊室……让这些话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逼人们不得不听见。”
小梅眼睛一亮:“就像病毒传播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