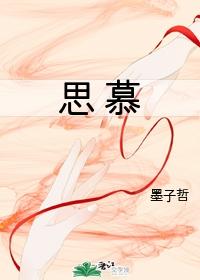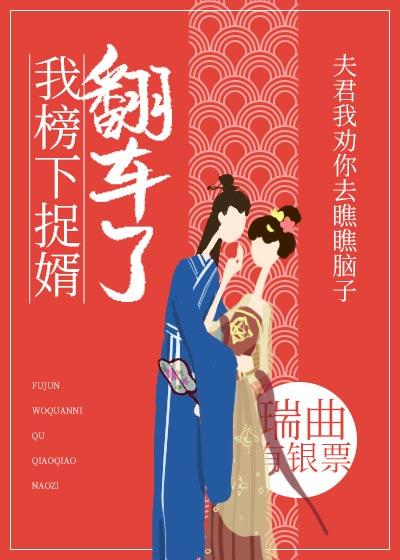笔趣阁>贫道要考大学 > 第188章 备战(第2页)
第188章 备战(第2页)
“不,”陈拾安摇头,“是让光钻进裂缝。”
雨下了三天三夜。第四天黎明,阳光刺破云层,照在湿漉漉的山路上。一辆破旧面包车驶入村庄,车身上贴着“流动图书车”字样,实际是民间公益组织改装的心理援助移动站。司机下车时递给陈拾安一封信,来自贵州铜仁的一所山村小学:“你们的‘心跳树脂片’我们收到了。孩子们轮流听了那段录音,有个小女孩哭了,她说原来别人也会害怕妈妈不要她。”
陈拾安把信收好,转身却发现阿岩站在屋外,手里紧紧攥着什么。
“老师,我想加入‘倾听者训练营’。”
“你还小。”
“我已经十一岁了。”阿岩抬起头,眼神坚定,“我知道自己帮不了太多人,但我可以听。我可以让他们知道,有人在。”
那一刻,陈拾安仿佛看见十年前的自己??那个蹲在福利院走廊尽头,只为等一个孩子愿意开口说话的年轻人。他曾以为拯救需要宏大方案,后来才明白,真正的改变始于一次低头、一句回应、一个愿意停留的身影。
他点点头:“好。但你要记住第一条法则。”
“我知道。”阿岩轻声背诵,“**倾听不是拯救,而是陪伴。**”
当天下午,陈拾安召集所有核心成员召开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应对即将出台的《青少年心理服务数字化建设指南》草案。这份文件由某互联网医疗平台幕后推动,拟在全国中小学推广AI情绪监测系统,通过摄像头、手环、课堂行为分析等手段实现“早期预警全覆盖”。
“他们打着预防自杀的旗号,实则构建全景监控网络。”小梅展示一份内部流出的技术白皮书,“学生的每一次皱眉、走神、沉默都会被打上标签,生成‘心理风险指数’,自动推送给班主任、家长甚至教育局。”
“然后呢?”陈拾安问。
“然后学校为了降低‘高危学生比例’,会优先处理那些容易暴露问题的孩子??比如常独处的、成绩差的、家庭背景复杂的。而真正危险的环境因素,比如校园霸凌、教师言语暴力、家庭忽视,反而被忽略。”
“因为他们要的是数据达标,不是人心复苏。”陈拾安冷笑,“这套系统上线之日,就是千万孩子学会伪装之时。”
他站起身,在墙上挂起一张全国地图,开始插旗。每一面小旗代表一个已知的“地下倾听站”??如今已有四百一十六个,遍布三百多个县市。它们没有经费、没有编制、没有官方认证,却靠着最原始的方式运转:纸笔、口述、面对面交谈。
“我们要建一座反向数据库。”他说,“不记录症状,不标记风险,只收集‘被听见的瞬间’。”
“怎么做?”石头问。
“发起‘千声计划’:邀请每一位曾被倾听的人,录制一段不超过三十秒的声音??可以是一句话、一首诗、一段笑声,甚至只是呼吸。我们不做分析,不建模型,只把这些声音刻成实体唱片,送往每一个乡村学校、社区中心、流浪儿童救助站。”
“让人们知道,”他目光灼灼,“心理健康的标志不是‘零风险’,而是‘敢说话’。”
计划启动当晚,第一段声音来自云南怒江的女孩李芸??三年前她在录音机里说“我想死”,如今她已是师范生,录音中她说:“老师,我现在每天早上都会对镜子说一句话:‘我在,所以我值得活。’”
第二段来自一位农民工父亲,在工地宿舍录的音:“儿子打电话问我为啥总不回家。我没忍住哭了。以前我觉得男人不能哭,但现在我知道,哭出来,孩子反而更懂我。”
第三段是新疆喀什的小学生们合唱的一首童谣,歌词是她们自己编的:“月亮听见我说话,星星也听见啦,我不怕黑了,因为我有朋友啊。”
这些声音被刻成黑胶唱片,封面印着一句话:“此唱片无法变现,不能评分,不宜用于考核??仅供人类互相听见。”
一个月后,首批一千张唱片送达各地。有学校将其放在图书馆角落,有社区中心在傍晚播放,还有学生自发组织“静听之夜”,关灯、围坐、闭眼,只为认真听完一首陌生人的呼吸。
与此同时,“百日筑墙计划”进入关键阶段。运营资金再度吃紧,服务器面临断缴风险。有人建议妥协:“哪怕暂时接入资本的数据接口,先保住系统运行?”
陈拾安拒绝:“我们可以关站,但不能变质。”
就在最艰难时刻,一封匿名邮件抵达小梅邮箱。附件是一段视频,拍摄于某大型互联网公司内部会议。画面中,一名高管直言:“‘夜语亭’模式不可复制,也不可持续,等他们资金链断裂,用户自然流向我们的平台。届时我们只需收购其品牌残值,包装成‘公益IP’即可。”
镜头扫过会议室,墙上挂着标语:“**用科技重塑人性效率。**”
视频末尾,一行字浮现:“致陈拾安:你们坚持的东西,正是我们最恐惧的东西??因为它无法被量化,也无法被控制。”
陈拾安看完视频,沉默良久,然后笑了。他拿出录音机,放入新磁带,按下录制键:
“各位,我是陈拾安。今天是四月二十二日,谷雨。田里的秧苗开始抽芽,山间的雾气还未散尽。我想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