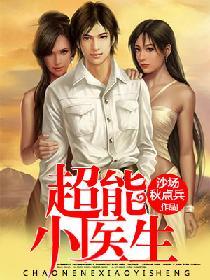笔趣阁>王妃,请自重 > 第206章泼辣无罪(第1页)
第206章泼辣无罪(第1页)
“跪下再和本爵爷说话~”
“。。。。。。”
余博闻也是要面子的,声音因愤怒而微微发颤,“楚县公休要欺人太甚!堂堂开国男,颠倒黑白,竟只会在此与后宅妇人逞口舌之利么?”
丁岁安闻言,反。。。
雪落无声,却压弯了归途塔檐角的铜铃。那铃音久未响动,仿佛也被这岁月封存,只在风最冷时轻轻一颤,像是叹息。
十年光阴如灯焰摇曳,不觉已逝。
如今的长安城,早已不再有“守烛人”之名。丁岁安的名字被刻在百姓口中的传说里,沈清璃的身影则隐于市井之间,像一缕春风拂过人间,不留痕迹,却处处生暖。
她依旧住在归途塔旧址改建的小院中,青瓦白墙,梅树临窗。每日清晨扫阶、煮茶、晾晒经卷,偶尔去城南医馆为贫苦者施药。人们唤她“梅娘”,不知其来历,只道这位女子心善如水,目光澄明,似能照见人心深处的寒凉。
而那盏曾贯穿天地的琥珀灯,早已熄灭。但万家灯火依旧长明,仿佛冥冥之中,仍有人默默守护。
这一夜,月隐星沉,乌云蔽空。
沈清璃独坐堂前,手中摩挲着一只旧陶杯??那是丁岁安生前最爱用的粗瓷杯,杯沿豁了一小块,他总说:“缺口处喝茶最顺口。”如今杯中无茶,唯有半寸清水映着窗外天光,微微晃动。
她忽然蹙眉。
水波之中,竟浮现出一行扭曲的字迹:
>“你还记得真正的你吗?”
她指尖微颤,立即将杯推至案边。可那水纹未散,反而出现在屋角铜盆、灶台水瓮,乃至檐下雨滴之上。每一滴水中,皆浮现同样质问。
这不是幻觉。
这是“影契”的余烬,在时间尽头悄然复苏。
她闭目凝神,识海翻涌。十年太平,并非终结,而是蛰伏。当年丁岁安以命燃灯,将影契本源封入极北归灯塔地底裂缝,用双魂誓约之力镇压。可信念若松,封印自裂。如今世人虽尚信灯火,却不复昔日虔诚。香火渐淡,愿力稀薄,那道血纹正缓缓苏醒。
更可怕的是,它开始质疑她的“真实”。
“你还记得真正的你吗?”??这句话如针刺魂。
她确是因万民信念而生,但她也是真实的沈清璃。她记得幼年母亲教她缝香囊的模样,记得第一次与丁岁安并肩破阵时指尖相触的温度,记得他在病中咳血仍坚持抄录《灯律》的背影……这些记忆如此清晰,怎能是虚妄?
可若真是虚妄呢?
她猛地睁开眼,望向墙上挂着的那幅白绢诗笺。上面四句诗仍在,墨色温润:
>风雪何须惧夜寒,
>一灯如豆照心安。
>若问真伪何处辨?
>可曾为君留碗筷?
可此刻,最后一句的“碗筷”二字,竟渐渐褪色,化作灰烟消散。
她心头剧震。
这是“共感侵蚀”的征兆??当群体认知动摇,个体存在的根基便会被悄然抹除。十年前那一场风波,靠一碗热粥、一盏门灯挽回信任;可今日,人心浮躁,速食成风,谁还会为晚归之人留饭?谁还会在寒冬为陌生人添柴?
她起身推门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