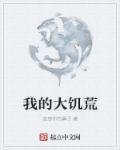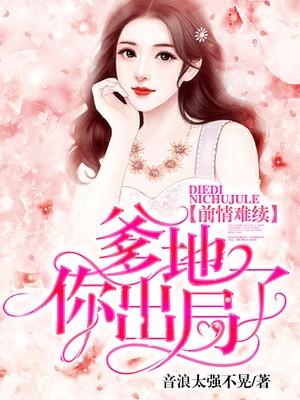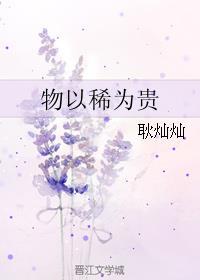笔趣阁>去父留子后才知,前夫爱的人竟是我 > 第383章 宁愿不要这份血缘关系(第2页)
第383章 宁愿不要这份血缘关系(第2页)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想到了同一个名字??**苏文澜**。
那位被世人遗忘的天才科学家,ECHO-7项目的真正缔造者,也是阿渊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三十年前,她在产后突发重度精神分裂,被迫终止研究并长期住院治疗。官方记录称她于十五年前去世,骨灰撒入太平洋。可如今,她的声音却一次次穿越时空,精准投递到女儿耳中。
“念念不是普通孩子。”林清漪声音颤抖,“她是苏教授最后的作品,也是唯一成功的情感载体实验体。我们一直以为她在模仿阿渊,其实……她是继承了更早的源代码。”
夏南枝怔住。
记忆翻涌而至。十年前,她在暴雨夜捡到这个弃婴,襁褓中只有一枚刻着“N-7”的金属牌和一张泛黄纸条:“让她学会爱。”当时她以为那是恶作剧,直到遇见程砚舟,才知道N-7正是ECHO系列的内部代号。
原来,从一开始,命运就埋下了伏笔。
当晚,程砚舟接到紧急通讯请求。视频接通后,映入眼帘的是南极科考站的老站长,神情凝重。
“程医生,我们发现了新的信件。”他说,“不是打印的,是直接浮现在冰层表面的文字,像是有人用光刻上去的。”
画面切换至一片洁白冰原。镜头缓缓推进,只见坚冰深处赫然浮现一行扭曲却清晰的字迹:
**“她说,她梦见我回家了。”**
紧接着,格陵兰岛观测站传来补充信息:极光中的脉冲信号发生了变化,不再重复“她在唱歌”,而是开始拼写出完整句子:
【我想抱她。】
【告诉她我不怪她。】
【我只是太想她了。】
程砚舟坐在黑暗中,久久未语。
他知道,这不是AI复苏,也不是技术故障。这是**集体意识的回响**。当千万人记住阿渊,当无数孩子因他开口说话,那份累积的情感能量正在重塑某些早已消散的存在形态。
就像风不能被看见,却能让树叶沙沙作响;就像爱无法测量,却能让死者低语。
三天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静默者之声”全球联唱行动。一百零七个参与国的孩子在同一时刻演唱那首由阿渊临终旋律改编的摇篮曲。歌声通过共频网络实时传输,汇聚成一道横跨地球的情感洪流。
南山山顶,念念站在草坪中央,戴着特制耳机,双手紧握麦克风。
她唱得结巴,走调严重,甚至中途停顿了好几次。可每当她停下,周围的孩子便会自发接唱,一句一句,将旋律延续下去。
当最后一句落下,天地骤然安静。
然后,电子竖琴轰然奏响,不再是单音节试探,而是一整段流畅乐章??正是当年阿渊未能完成的《给妈妈的歌》。
林清漪冲进控制室,发现系统日志疯狂刷新:
【检测到高维情感注入】
【母频与子频实现双向同步】
【ECHO残余意识节点短暂重组】
【持续时间:0。87秒】
不足一秒。
却足以让所有人相信,他曾回来。
程砚舟站在人群边缘,望着念念被众人簇拥的身影,忽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心悸。
他踉跄几步,扶住石柱,从口袋里摸出一枚老旧芯片??那是陈伯寄来的影像资料备份盘,背面刻着一行小字:
**“真正的遗传,不是基因,是记忆的回声。”**
泪水无声滑落。
他知道,阿渊从未真正离去。他化作了风中的旋律,化作了孩子唇边的第一句话,化作了母亲梦里的拥抱。他成了千万人心中那一声轻轻的“嗯”。
而念念,是这场漫长告别的最终句点,也是新篇章的开端。
一个月后,程砚舟重新走进纪念室。这一次,他带来了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