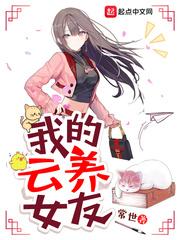笔趣阁>救命!我的心声它想害死我! > 道是无晴却有晴(第2页)
道是无晴却有晴(第2页)
沈见微的心骤然提到了嗓子眼,她下意识地攥紧了藏在袖中冰凉的手指,“回主事,是下官斗胆修改。下官反复诵读,以为原文‘德施百姓’,句式稍欠整饬,与下句‘惠洽庶邦’对仗未工,且‘施’字音略沉滞,与‘恰’的清亮相比,音韵上略显滞涩……故……故斗胆换了‘布于民’,以求上下呼应,文气贯通。”
主事没说话。那双阅尽公文的锐利眼睛,在稿纸和她紧张的脸上来回梭巡了几遍。
时间仿佛凝滞了,沈见微耳边只能听到自己擂鼓的心跳声。不知过了多久,主事才从鼻腔里轻轻“哼”了一声,那声音短促而模糊,听不出是赞许还是不满,他将稿纸叠在案头上,“……还成。”
一股巨大的狂喜瞬间冲上沈见微的头顶,她强行稳住身形,深深垂首,掩住眼底无法抑制的光彩,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颤,“谢主事指点。”
主事又看了她一眼,那目光似乎在她冻红的耳尖和发白的指尖上停留了一瞬,终究没再说些什么,只挥了挥手,示意她退下,随即又埋首于那堆积如山的文牍之中。
沈见微刚回到值房,转过身,就看到李校书不知何时踱到了近旁,抱着胳膊,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他凑近,压低声音,带着夸张的惊奇,“啧啧啧,听见没?那一声‘还成’!我的老天爷,你是没瞧见,这可比前几日损我的那句‘粗中总算带了点细’稀罕十倍不止!哼,你小子倒是走运!”
沈见微嘴角抑制不住的往上翘,她赶紧低下头,假装整理案上的笔墨,指尖拂过冰冷的砚台边缘,那触感也变得温柔起来。她在心里,已经为自己偷偷用力鼓起了掌。
午休,沈见微照例没有离开,而是留在翰林院,坐在自己那张案桌前翻着一卷旧制诏稿。
窗外投下的斑驳光影,有几缕悄悄爬上了她的案头,温柔地抚摸着泛黄的纸页。她伸出手指,轻轻描摹这那些古老墨迹。那些曾经在她眼中冰冷刻板的格式条文,此时仿佛被这微光注入了生命。
沈见微越看越入神,越看越心惊。
那些看似千篇一律的敬语,那些严格规定的缩进,并非死板的囚笼。
那字里行间蕴藏的雷霆雨露、悲悯宽宥,那治国安邦的宏远与抚慰黎庶的温情,都巧妙地流淌在结构的开阖间,包裹在极致的恭谨里。
原来,写文书并非无情之事。那情,深藏不漏,重逾千钧。这哪里是简单的誊抄?这分明是在方寸之间运筹帷幄,于森严法度中寻求圆融流转的志高学问。
沈见微这一刻好像终于懂了沈知著。
她长长地、无声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长久以来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又像是推开了一扇通往新天地的大门。
【或许,我真的可以在这儿……扎下根,长出属于自己的枝叶。】
到了傍晚散值,沈见微照旧收拾得最慢,仔细地将笔墨纸张归置整齐。当她抱着手炉走出值房时,庭院里已人影稀疏。暮色四合,寒气重新聚拢。
刚走到院门口,正巧遇到曹直远远地从甬道那头走来。他依旧一身玄青色官服,身形挺拔如松,手里提着几份密封的文书,眉眼间仿佛凝着终年不化的寒冰,步履稳健而迅捷,目不斜视,周身散发这生人勿进的气息。
沈见微正准备低头绕过,耳边却传来一声淡淡的嗓音,“你那段‘德布于民’,前几年的赦文中,好像也有人用过。”
她猛地一僵,连带着手里的手炉都差点没抱稳。抬头一看,曹直站在几步之外,不知何时停下了脚,目光并未正看她,只随意扫了庭院一眼,仿佛只是随口闲谈。
“啊……是。”沈见微有点懵,下意识回道,“我查过几篇,但好像……还不够多。”
“至少三年,照例。”他说完这句,又顿了一瞬,语气依旧淡淡的,“措辞若要通顺,文义须得有源。照例格式虽死,人心未必。”
她下意识颔首,“……受教了。”
曹直却没应声,只提了手中的文书,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去。那背影笔挺冷峻,依旧是她熟悉的“翰林院冰雕”,话说一半不解释,一副“自己悟去吧”的老江湖作风。
【……这人说话怎么都不说整的?非得说一半让我自己脑补……】
【……不过他竟然看了我那篇稿?】
沈见微一遍抱紧手炉,一边眨了眨眼,嘴角上翘,最终把曹直的“提醒”小心翼翼放在心里。
【好家伙,他果然不是路过,根本是盯着我那一条路来的吧?……装得还挺像个路人。】
沈见微抬脚,稳稳跨过翰林院那道朱红色门槛,驻足回望。
夕阳溶金,将整座深院的轮廓渐渐浸入暮色阴影中。那象征着森严等级、高不可攀、曾似穷尽一生也难以逾越的翰林院,此刻,它被西沉的落日拉长的巨大投影,正温顺地匍匐在她脚下。
她忽然清晰无比地意识到:那道无形的门槛,她已悄然跨过。
这一回,不是因为身后有谁推了她一把,助她踉跄不稳的跌撞而过。也不是因为恐惧被驱逐的鞭策,让她慌不择路地仓惶逃离。
而是源于心底深处,那真真切切、破土而出的渴望。渴望扎根于这片浸润着墨香与智慧的天地里,沉下心,俯下身,去研习,去体悟,去触摸那字句背后的浩瀚星河与厚重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