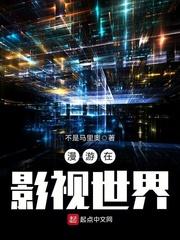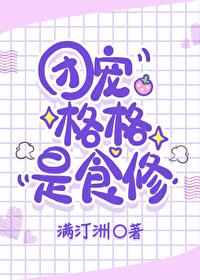笔趣阁>救命!我的心声它想害死我! > 道是无晴却有晴(第1页)
道是无晴却有晴(第1页)
翰林院的冬日清晨,冷得连砚台里的水都缩成了一团。
沈见微裹着厚厚的袍子,像一只谨慎的狸猫,在院门还没完全打开的时,便侧身挤了进来,带进一股裹着霜气的寒风。
天色是沉沉的灰白,低低压着飞檐斗拱。偌大的翰林院庭院空寂无人,只有几株枯枝在风中发出细碎而尖锐的呜咽。
她找到自己那张靠墙的小案,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巧的手炉暖了暖冻僵的手指,才小心翼翼地拨开炭火,将一壶冰冷的茶水架上去慢慢温着。
眼圈下泛着淡淡的青影,鼻尖冻得通红,几乎要失去知觉,沈见微却浑然不觉,只神情专注地摊开那本厚重卷边的《翰林文书格式通例》。
指尖特有的干燥气息和陈年墨香弥漫开了,她提起笔,蘸了蘸尚未完全化开的浓墨,屏息凝神,一笔一划地誊抄着,姿态专注得近乎虔诚。
如今,她已经不再依赖当初进翰林院时,像拾荒般东拼西凑整理出来的那本参考稿了。那东西如同拐杖,好用是好用,可终究是别人的筋骨支撑。
她得把这套规矩、这份手艺,真真正正地融进自己的骨血里,学到自己手上,才能立得住。
“哇——!”窗外光秃秃的老槐树上,一只寒鸦蓦地嘶叫一声,声音凄厉突兀。沈见微惊得一颤,一滴墨险些落在纸上。
她懊恼地蹙眉,随即甩甩有些发沉的脑袋,仿佛要将那些关于前途未卜的焦虑、关于他人眼光的揣测,统统甩进这凛冽的空气中。
“哟!这是谁起得比报晓的鸡还早啊……沈编修?”一个带着弄弄睡意的声音打破了沉寂。进来的正是李校书。
他裹着一身半旧不新的墨色大氅,毛领子有些翻卷,顶着一头桀骜不驯的鸡窝头,一边打着能看见后槽牙的哈欠,一边揉着惺忪睡眼打量她,“大早上连个鬼都没有?你趴在这里干嘛呢?冻冰雕?”
李校书凑近定睛一看,等到他看清她手中的册子,颇为惊奇地看了沈见微一眼,“大早上来……背书?”他尾音拖得长长的,带着点戏谑。
“快了,”沈见微抬起头,朝他绽开一个诚恳的笑容,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氤氲开,“再给我半个时辰,我就能把格式通例四十五条全背下来了!”
李校书的目光扫过她冻得通红几乎透明的鼻尖,又落在案上那密密麻麻却工整异常的墨迹上,原本还带着睡意的眼睛瞬间瞪得滚圆,“嚯!你这劲头……是真铁了心想留在这翰林院?”
“当然是想啊。”她答得毫不犹豫,眼神清亮,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盼,“要不……您来抽问几条?权当帮我醒醒神。”
李校书“啧”了一声,像是被她的认真劲儿逗乐了。
他慢悠悠地从大氅内袋里摸出一个磨得油亮的文案折子,随手翻开,眼皮都没怎么抬,声音懒洋洋地问道,“行,那……大景制诏格式,起首如何?”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沈见微脱口而出,没有丝毫迟滞。
“嗯,”李校书不置可否,翻了一页,“那……诏令中若有赦宥条目,行文规矩如何?”
“需另起一行,格式左顶空两格。”她依旧对答如流,声音平稳。
李校书抬头瞥了她一下,似乎想加点难度,“若为抚慰震灾,布告天下,结尾需附何语?”
“欽哉,布告中外,使咸知悉。”她答得斩钉截铁,语速流畅,甚至不等对方反应,又自然的补充道,“若为特赦诏书,依例需加‘朕恻然悯焉,宜敕所司体予朕意’,置于‘使咸知悉’之前。”
李校书定定看她一眼,这才缓缓合上折子,发出一声轻响。
“哟,”他拖长了调子,嘴角似乎牵动了一下,“倒是背得挺像回事,条理也清楚,看来这冷风没白喝。”
沈见微只觉得胸腔里有一小团暖流猛地跃动起来,几乎要冲破喉咙。她赶紧垂下眼睫,用力抿了抿唇,压下那份雀跃,努力装出一副“我不过是尽了本分”的沉稳模样,微微欠身道,“是李校书平日指点得法,下官只是依样画瓢罢了。”
她知道,这位看似备懒的前辈,眼光其实刁得很,轻易不会说句软话。
日头渐高,惨淡的冬日暖阳终于艰难地穿透云层,在冰冷的青砖地上投下几道模糊的光影。主事大人终于踩着这稀薄的光线姗姗来迟。
他面色如常,手里抱着厚厚一大摞奏折文书,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臂弯里。
人未进值房门,那惯常的声音已经先到了,“沈编修——前日交办你的那份诏书例稿,格式可理顺了?午时之前必须呈来!”
“回主事,已誊录完毕,请您过目。”沈见微早已候着,闻言立刻上前,双手将那份用镇纸压得平平整整的稿件恭敬奉上,腰身弯成一个标准的弧度。
主事接过,没看她,径直走到自己的大案后坐下。他展开稿纸,目光扫过一行行字迹。他看得极快,沈见微屏住呼吸,目光落在主事大人紧抿的嘴角和习惯性微蹙的眉心上——这次居然没皱眉?
这份平静,于她而言,已是今日来最高的“官评”。
“嗯?”主事的手指忽然顿在纸页中段,指尖重重地点了一下,“这一句‘今以德布于民、惠洽庶邦’……是你改的?”他抬起头,目光直射沈见微,“我原文我记得清楚,是‘德施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