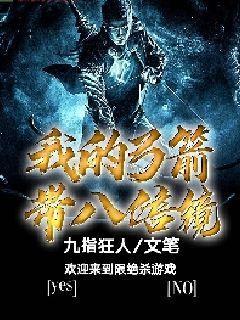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屁股坐正了吗?你就当导演 > 第161章 百花之哗然韩三品不装了(第1页)
第161章 百花之哗然韩三品不装了(第1页)
9月13日,大连。
第2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闭幕式在大连举办。
大连是个好城市,时值初秋,凉爽异常。
曹忠带着《南京照相馆》剧组莅临大连。
“曹导,好久不见。”
酒店之中,。。。
戈壁滩上的风,从不停歇。它卷着细沙,在天地间织成一张金黄的网,把一切都裹进无边的寂静里。周舟坐在地质勘探队的皮卡后座,头抵着车窗,任砂砾敲打玻璃,像某种远古的密语。车子颠簸前行,仪表盘上的指针微微颤抖,如同他们此行的命运??未知、脆弱,却执拗向前。
张小宇在副驾翻看那份影印档案,眉头越皱越紧。“你看这里,”他指着模糊的一行字,“‘黄沙旅’编制代号为‘07-9’,隶属国防科委直属后勤协调组,任务周期七十二小时,人员构成标注为‘临时抽调’。”他冷笑一声,“又是临时工。”
杨蜜坐在周舟身旁,耳机里循环播放着苏和最后那句口述:“只要灯不灭,我们就还能回家。”她轻声说:“这次的任务更狠。核爆刚结束就冲进去,等于往辐射汤里跳。他们不是死于事故,是明知必死而赴之。”
周舟没说话,只是从包里取出一只旧铁盒。打开后,里面是一块灰白色的石头,表面布满焦痕,边缘呈放射状裂纹。这是他在阿尔山展览闭幕时,一位匿名老人托人送来的遗物。“据说是王振国埋在营地废墟下的纪念石,上面刻了十七个名字。”他说,“可现在我们知道,实际牺牲的不止三十四人。还有更多,连名字都没留下。”
手机震动。是敦煌那边联络员发来的新消息:“已确认司机后代叫陈卫东,现居玉门老城,经营一家修车铺。其父陈大山,1964年被铁路局借调至酒泉基地,三个月后病亡,死因登记为‘急性肝坏死’,但家属回忆他全身溃烂,头发脱落殆尽。”
“典型的辐射病。”张小宇喃喃道,“可那时候没人敢提‘核’字。”
车队驶入玉门老城时,天色已暗。这座曾经因石油而繁荣的小城如今沉寂如墓,街道两旁的招牌大多残破不堪,唯有几家羊肉馆还亮着灯。他们在一家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便按地址找到了陈卫东的修车铺。
铺子藏在巷子深处,门口堆满报废轮胎和锈迹斑斑的发动机零件。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弯腰拆卸变速箱,满脸油污,手指粗短变形,显然是常年与金属打交道的结果。听见脚步声,他抬头看了眼,眼神警惕。
“您是陈卫东先生?”周舟上前一步,递上身份证和纪录片项目书。
男人接过看了看,沉默片刻,忽然冷笑:“又是来问那个事的?”
“我们想了解您的父亲,陈大山同志。”周舟语气平缓,“他是‘黄沙旅’的一员。”
陈卫东猛地站直身子,手里的扳手“哐当”掉在地上。他盯着周舟,声音陡然拔高:“谁告诉你们这个名字的?!我爹一辈子没提过半个字!连我妈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但我们知道。”杨蜜轻声说,“我们知道他在罗布泊,在核爆之后第一个冲进核心区,回收数据舱。我们知道他回来时已经不成人样,也知道他临死前一句话都没留下。”
陈卫东的身体晃了一下,扶住墙才没倒下。他咬着牙,眼里泛起红光:“你们知道什么?你们知道我六岁那年抱着我爸哭,他身上全是黑血,皮肤一块块往下掉吗?你们知道我妈烧了他的衣服,整整烧了三天,说怕邪气沾身吗?!”他的声音嘶哑,“可到现在,民政局连抚恤金都不给,说‘非编制、非战斗、无可考’!”
空气凝固。
周舟缓缓从铁盒中取出那块焦石,放在桌上。“这块石头上,本来有十七个名字。后来我们查到,其中三个正是当年‘黄沙旅’的地勤人员。赵志明、孙建国、刘文海。他们的档案在地方志办尘封了五十年,直到去年才被人偶然发现。”
陈卫东怔住了。他颤抖着手摸向石头,指尖划过那些刻痕,仿佛触到了父亲未曾说出的遗言。
“我们不是来索取什么的。”周舟说,“我们只想让世人知道,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蘑菇云升起后逆向而行。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连一张合影都没有。但他们用生命带回了第一手数据,让中国挺直了脊梁。”
良久,陈卫东抬起头,眼中泪水滚落:“我爸走前,只说了两个字??‘值了’。”
一行清泪滑过沧桑脸颊,砸在冰冷水泥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痕迹。
当天下午,陈卫东带他们去了老家祠堂。那是一座建于民国的老屋,青砖灰瓦,檐角雕花早已风化。正厅中央供奉着祖先牌位,而在最角落,立着一块无字碑,碑面光滑,未刻一字。
“每年清明,我妈都让我烧纸钱,念一句:‘爹,国家知道您去了哪儿吗?’”陈卫东低声说,“她说,活着的人可以瞒,但祖宗得知道真相。”
周舟跪了下来,双手捧起那块焦石,轻轻放在碑前。然后,他拿出笔墨,在宣纸上写下一行字:
**陈大山,甘肃武威人,1938年生,1964年参与罗布泊核试验地勤保障任务,因公殉职,年二十六。**
他将纸条压在香炉下,点燃三支香,深深叩首。
那一刻,风穿堂而过,吹动檐铃轻响,仿佛回应。
离开玉门后,团队驱车前往罗布泊腹地。沿途荒无人烟,偶见废弃观测站遗迹,钢筋骨架裸露在外,像巨兽骸骨。GPS信号时断时续,全靠勘探队老李凭经验引路。第三天傍晚,他们终于抵达当年数据舱回收点??一片干涸盐湖中央的混凝土平台,四周散落着烧熔的金属残片。
“就是这儿。”老李指着地面一处凹陷,“当年有个临时指挥棚,爆炸后塌了。据说最后一批进去的人,是从这里抬出三个密封箱,然后全员撤离。再后来……就没人提了。”
夜幕降临,气温骤降。他们在平台上搭起帐篷,围坐取暖。张小宇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刚刚整理好的名单:**陈大山、赵志明、孙建国、刘文海、周德福、马青山、李国强、吴建军、胡胜利、田有财……共二十一人**。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被掩埋的人生。
“这些人的家属,能找到几个?”杨蜜问。
“目前联系上七个。”张小宇叹气,“其他要么绝户,要么迁徙失联。有个女儿说,她爸临终前反复念叨‘别让人忘了西线的事’,可全家都不懂什么意思。”
周舟望着星空,忽然道:“明天,我们去马鬃山。”
“为什么?”杨蜜不解。
“因为那里有个老兵守墓人。”周舟说,“据陈卫东说,有个姓林的老兵,曾在基地服役,退休后自发守护一片野坟。当地人称那地方为‘无名坡’,说是埋了些‘搞试验的外调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