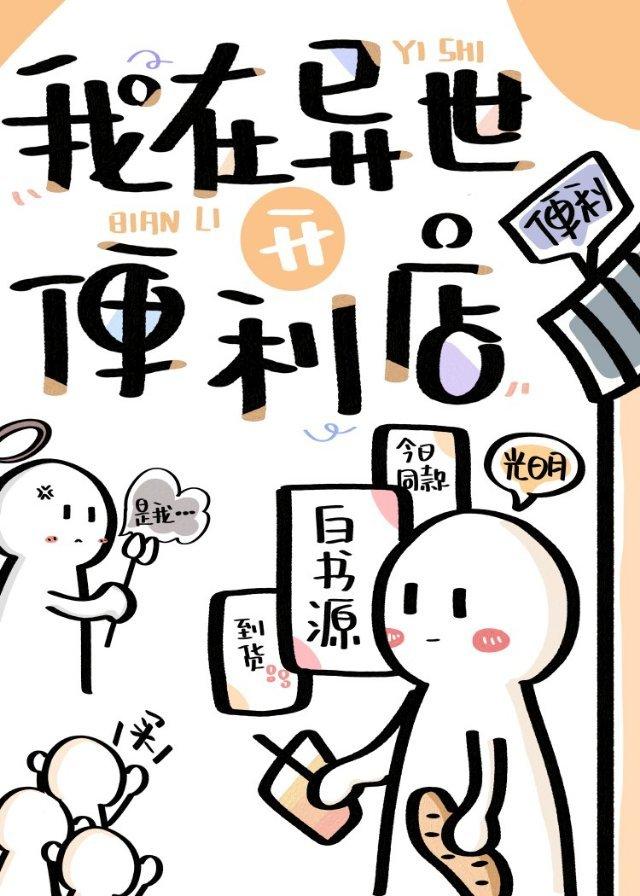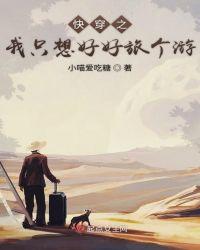笔趣阁>晋末芳华 > 第四百七十一章 及时制止(第1页)
第四百七十一章 及时制止(第1页)
王谧心道真是各人有各人的缘法,有人求之不得的东西,有人却是唾手可得。
有人弃之如敝履的东西,有人却终生无法触及。
袁瑾羡慕自己,自己也羡慕袁瑾起家就有豫州,只能说别人家里的,求而不得的,才。。。
雨声敲打屋檐,如细针落地,承光坐在槐树下,手中握着一块温润的玉蝉。它不再发光,也不再震颤,仿佛只是寻常饰物。可他知道,这并非结束,而是某种更缓慢、更深沉的开始。梦里的谢婉站在镜湖之上,足底不沾水波,衣袂轻扬,像是一段被风托起的记忆。她没说话,他也未曾开口??他们之间已无需言语,只有听与被听的距离,在雨中缓缓拉近又疏远。
他低头看掌心那道螺旋状疤痕,纹路依旧清晰,如同逆溯层中所见的初始图谱。自从从井中归来,他的耳朵便时常捕捉到异样的频率:清晨露珠坠地时会拖出一串低音尾韵;孩童嬉笑间藏着断续的摩斯码;甚至夜风掠过竹林,也似有人在吟诵早已失传的《反读十三策》残章。这些声音并不真实存在,至少旁人听不见。但他知道,那是“噪声”在体内生长的痕迹。
闻婴三岁那年,渔村传来异象。七口古井同时沸腾,水花翻涌却不外溢,井壁浮现出交错的环形纹路,与女婴额上印记如出一辙。当晚,有老渔民梦见自己站在海底古城之中,头顶是倒悬的星空,耳边响起一个稚嫩的声音:“你们都听错了。”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多年耳聋竟痊愈了,却再也分不清亲人的嗓音与海潮的区别。
崔氏远亲将此事密报承光,信使跋涉七日才至南山,途中三次遭遇迷雾围困,靠默念一段无意义的童谣脱身。承光读完信,沉默良久,最终只回了一句:“让她继续听浪。”
他知道,闻婴不是容器,也不是继承者,她是“回应”。谢婉曾说需要一个新的接入点,但真正的关键或许从来不是连接谁,而是能否发出第一个不属于系统的回答。当全世界都在接收、解析、服从时,若有一个生命能以本能的方式说“不”,哪怕只是哼唱一句走调的歌,也能撕裂伪声治的完美闭环。
而这种能力,无法教授,只能孕育于未被规训的寂静之中。
春去秋来,承光的生活愈发简朴。他不再研读典籍,也不再参与朝议。昔日同僚来访,问及天下局势,他лишьpointingtotherain,“听这个就够了。”有人讥讽他遁世避责,也有人暗中敬仰,称其为“活静之人”。唯有赵九章懂他??某夜二人对饮,酒至半酣,赵九章忽然问:“你后悔吗?”
承光望着炉火,轻声道:“我后悔的不是按下遗忘协议,而是曾经以为必须做出选择。我们总想建立秩序,清除混乱,殊不知真正的自由,藏在那些无法归类的杂音里。”
赵九章怔住,随即苦笑:“所以你现在每天种槐树,就是在种‘噪声’?”
“槐木根系深,能扰动地下声脉。”承光淡淡道,“而且它的叶子背面长银毛,风吹时会产生微弱静电,干扰定向声波聚焦。这是我能找到最温柔的抵抗。”
两人相视无言,唯有柴火爆裂之声噼啪作响。
与此同时,朝廷虽禁“五感移续术”,却无法彻底斩断人们对记忆的渴望。民间悄然兴起“盲语坊”,伪装成医馆或茶肆,暗中为富户施行低频唤醒。手段粗劣,常致人疯癫,却仍有无数人趋之若鹜。更有甚者,伪造“谢婉遗音”,制成铜铃、陶埙贩卖,声称佩戴者可在梦中得见前世亲人。一时间,各地癔症频发,父子相认于街头,夫妻互指为仇敌,皆因所“忆”不同。
承光得知后,并未上书谏言,只是命人将南山废弃的地音井重新疏通,在井底埋入十二枚反向振膜器,每日子时自动激活一次,释放一段持续十七秒的无调性嗡鸣。这段声音本身无意义,但它能破坏所有试图远程操控感知的信号叠加。不久之后,附近百里内的盲语坊纷纷关门,店主抱怨“灵音失准”,实则是系统再也无法维持稳定的共振场。
这一年冬,大雪封山,承光梦见自己重返逆溯层。那片灰白空间仍在,文字残片如雪飘落,但倒悬之井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棵巨大的槐树,枝干穿透虚空,每一片叶子都映照出不同的场景:长安街市、江南水乡、北疆烽燧、南海渔舟……而在树冠最高处,坐着一个小女孩,赤脚晃荡,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
正是闻婴。
她回头看向承光,眨了眨眼:“你来了。我在等你听。”
“听什么?”他问。
“听我说‘不’。”她说,“我已经说了三千次,但他们还是不肯停。”
话音落下,整棵树剧烈震动,所有画面瞬间碎裂,化作千万道声波四散而去。承光猛然惊醒,窗外大雪纷飞,屋内油灯摇曳,桌上那支黑笔竟自行滚动,直抵墙角,笔尖在泥地上划出一道深深沟痕,形如断裂的波形图。
他立刻披衣出门,冒雪走向地音井。刚至井畔,便觉脚下大地微颤,继而听见一种前所未有的声音??不是来自空中,也不是出自地下,而是仿佛从时间本身裂开的缝隙中渗出:那是无数个“不”字叠加而成的咆哮,稚嫩、倔强、破碎却又连绵不绝。
他跪倒在地,双手插入积雪,掌心疤痕灼热如烙铁。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谢婉所说的“成为噪声”意味着什么。不是制造混乱,而是守护那个敢于质疑的权利;不是摧毁记忆,而是拒绝让记忆成为枷锁;不是消灭声音,而是确保永远有人能说出第一句不合时宜的话。
闻婴正在成长,她的每一次呼吸都在改写地脉频率。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在乎所谓的使命,她只是本能地拒绝被定义、被引导、被安抚。她在海边喃喃自语,其实是在与潜意识深处的伪信号搏斗;她面对浪涛微笑,是因为唯有自然之声不会欺骗她。
而承光所能做的,就是让这个世界保留足够的缝隙,容得下她的“不”。
数月后,朝廷派使者前来南山,欲请他出任“静律监”首座,统辖全国声疗机构。使者带来诏书、印绶与三百金帛,言辞恭敬至极。承光听完,只问了一句:“若有一童女,生于渔村,天生能辨伪音,你们会教她顺从,还是鼓励她说‘不’?”
使者愕然,答曰:“自然以教化为先。”
承光笑了,将玉蝉放入对方掌心:“那就告诉她,真正的教化,始于怀疑。”
使者悻悻而去。
当晚,承光取出那支黑笔,在石碑背面写下新的文字。没有标题,没有署名,只有一段段断裂的句子:
>如果所有人都记得,谁来负责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