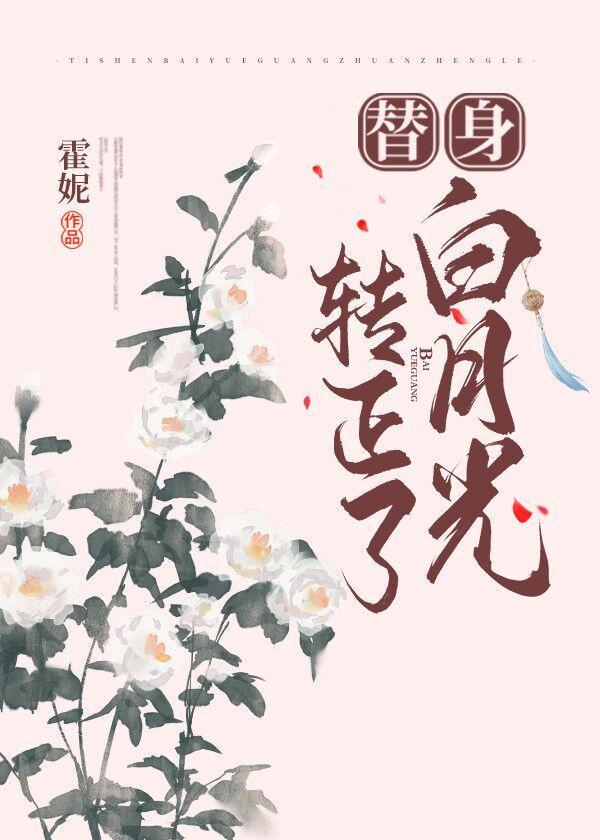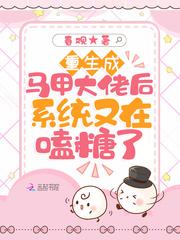笔趣阁>拾光予你 > 班长(第1页)
班长(第1页)
今安捏着那张突然传来的纸条,指尖微微用力,原本平整的纸张边缘因这细微的力道而泛起细密的褶皱,像他此刻被悄然搅乱的心绪。他慢慢展开,季予时的字迹跃然纸上,笔锋锐利,架构沉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一如他这个人。内容是请他放学后带自己熟悉一下校园环境。
一股微妙的暖流与巨大的惶恐同时涌上心头。心底里,因为那次河边的及时相救,以及随后在医院里感受到的短暂却真实的温暖,今安对季予时确实存有一份难以言喻的好感和潜意识的信任。这份源自于危急时刻伸出的援手和病榻旁无声陪伴所滋生出的情感,让他无法像竖起尖刺拒绝其他人一样,干脆利落地将季予时推拒在外。
但是,“一起逛逛校园”这种事,对他而言,意义远超过普通的同学交往。它意味着更长时间的独处,意味着需要不断地寻找话题,意味着要将自己置于一个相对开放且需要持续互动的境地里。这太过亲密,也远远超出了他为自己划定的、赖以感到安全的安全距离。他害怕这种近距离的、不经掩饰的接触,会暴露自己更多的不安、笨拙,甚至是那些他自己都不愿面对的、深藏起来的怯懦。更深的恐惧在于,他害怕自己会逐渐习惯甚至贪恋这份来自他人的温暖,而依赖,往往意味着软肋的形成,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猝不及防的失去。他早已习惯了失去前的拥有不过是短暂的幻觉。
他低下头,浓密的眼睫在白皙的脸颊上投下一小片阴影,掩去了眸中翻腾的复杂情绪。在纸条空白处,他缓慢而清晰地、一笔一划地写下五个字:抱歉,放学后有事。
他选择了一个相对温和的、社交礼仪上无可指摘的借口,没有直接回绝那个“不”字,避免显得过于生硬和不近人情,但拒绝的意思已然明确无误。他将纸条重新仔细折好,那动作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郑重。趁着讲台上的何老师转身面向黑板,粉笔与板面摩擦发出规律的“嗒嗒”声时,他轻轻伸出手臂,用指尖将那小小的纸团精准而快速地推回了季予时的桌角边缘,那个介于两人领地之间的模糊地带。
他甚至能感觉到,前排那个挺拔的身影在纸条触及桌面的瞬间,似乎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仿佛某种敏锐的感知系统被触发。几秒后,一只骨节分明、透着力量感的手伸了过来,动作流畅而稳定,无声地取走了那个承载着拒绝的纸团。整个过程没有眼神交流,没有言语,只有空气里弥漫开的一种无声的张力。
季予时没有回头,也没有再传来任何新的纸条,仿佛接受了这个结果。直到下课铃声响彻走廊,他利落地收拾好书本笔袋,站起身,才仿佛不经意般回头看了今安一眼。那目光深邃,如同古井无波,看不出是失望还是不悦,抑或是其他更深层的情绪,他只是淡淡地点了下头,算是打过招呼,便随着涌动的人流,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室。他的背影在人群中依然显眼,却带给今安一种难以名状的疏离感。
时间在一种略显沉闷的气氛中流淌,直到最后一节班会课的上课铃急促地响起,像是宣告着什么重要时刻的来临。班主任何孟准时踏着铃声走进教室,他脸上带着惯有的、憨厚而富有亲和力的笑容,但眼神里却比平时多了一丝审视与期待。
“同学们,安静一下。”他站在讲台后,双手微微下压,示意大家安静,“这节课我们进行本学期的班委选举。”他开门见山,声音洪亮,“班委是一个班级的核心和灵魂,是连接老师与同学的桥梁。我希望,有责任心、有热情、愿意为集体付出的同学能够踊跃参与,毛遂自荐或者推荐他人都可以。我们先从最重要的班长这个职位开始。”
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一种微妙的、混合着期待、观望、犹豫甚至是事不关己的氛围在空气中弥漫。有人低头假装整理书本,有人偷偷用眼神扫视四周,探寻着可能的竞争者,也有人跃跃欲试,但似乎在等待着第一个打破沉寂的人。
就在何老师环视全班,准备开口点名询问是否有自愿者时,一个清冷而坚定的声音,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清晰地打破了这片沉寂。
“何老师。”坐在前排的季予时举起了手,手臂伸直,姿态从容而笃定。在得到何老师示意的点头后,他从容不迫地站起身。他没有看周围任何带着惊讶或好奇目光的同学,目光平静地投向讲台上的何孟,语气沉稳有力,带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甚相符的成熟:“我想推荐今安同学担任我们班的班长。”
此话一出,不仅是教室里的其他同学纷纷露出惊愕的神色,交头接耳的低语声窸窣响起,连讲台上的何老师都明显愣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始料未及的惊讶。几乎是在瞬间,所有人的目光,带着探究、疑惑、好奇甚至是几分看戏的意味,不由自主地再次齐刷刷聚焦到教室后排那个总是试图将自己隐藏在角落、降低一切存在感的身影上。
今安原本正无意识地用笔尖在草稿纸上划着无意义的线条,闻声,握着笔的手猛地一顿,指尖因用力而微微发白。他随即缓缓放下笔,仿佛那支笔突然有了千斤重。他抬起头,脸上并没有明显的惊慌失措,更多的是一种被打扰了清净的无奈,以及眼底深处浓浓的、化不开的疑惑。他紧紧盯着季予时挺拔却显得格外固执的背影,眉头几不可察地蹙起,内心充满了不解与一丝被冒犯的愠怒:这人,为何总要一次次地、不由分说地将他从自己安全的壳里拽出来,推向那人前耀眼却令他无所适从的光束之下?
季予时仿佛完全没有感受到身后那道几乎要将他背影灼穿的、混合着困惑与薄怒的视线。他甚至微微调整了站姿,转向全班同学的方向,开始陈述他那听起来经过深思熟虑的理由。
他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每一个字都稳稳地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诚恳与笃定:“我推荐今安同学,并非一时兴起,或是出于任何私人关系的考量。”他顿了顿,目光沉稳地扫过在场或惊讶或不解的同学们,那眼神像是在安抚,又像是在宣告一个事实。
“首先,作为中考省状元,今安同学卓越的学习能力和极致的自律性,大家有目共睹。这份成绩代表的不仅仅是对知识的掌握,更是一种对卓越不懈追求的态度和扎实深厚的根基。我认为,这种对目标的专注和达成目标的能力,正是一个班长应该具备的基础素质,他能以身作则,为我们班级树立一个高标准的学习榜样。”
他的话语逻辑清晰,层层递进,仿佛早已打好了腹稿。
“其次,”季予时继续道,他的目光似乎在不经意间,极快地掠过今安那张因紧张和意外而更显苍白的面孔,随即迅速移开,语气变得更加肯定,甚至带着一种为之正名的力度,“或许有些同学觉得今安同学性格偏于安静,不善于或者不热衷于表达自己。”他微微提高了音调,“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他的优点——沉稳、不浮躁、善于独立思考和内省。班长需要的,从来都不是表面的夸夸其谈和一时兴起的热情,而是能够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能在纷乱中保持冷静、并理性分析处理事务的能力。我相信,在面对未来班级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需要决策的时刻,他的这种理性与沉静,会比任何冲动和盲目的热情都更有力量,更能做出对集体有利的判断。”
他几乎是在以一种不容反驳的方式,将今安的内向、不善交际的性格特质,重新诠释并拔高为一种难能可贵的、接近于领袖气质的沉静力量。
“最后,”季予时的声音里注入了一种更深的、几乎是带着某种信念感的力度,他再次看向何老师,也像是在对全班同学宣告,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我相信,一个人的责任心和担当,与他外表是否活跃、言语是否频繁,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今安同学或许不常表达,但他对待学习的严谨态度、对待每一件交付给他的事情的认真程度,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我认为他内心拥有着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秩序感,只是需要一個合适的机会被激发出来,需要一个能够施展的平台去展现。班长这个职位,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契机,不仅能让他用自己的方式为班级同学服务,贡献他的智慧和冷静,同时也能帮助他更好地打开自己,融入集体,在与大家的协作中,发掘自己身上那些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潜力和可能性。”
他这一番话,有理有据,环环相扣。既有对客观成绩的硬性肯定,又有对性格特质的深度解读和积极转化,最后更是巧妙地上升到了个人成长与集体贡献相互成就的高度。几乎是不留余地地将今安推到了一个“非他不可”、“舍他其谁”的位置上,字里行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推崇和极高的、甚至有些沉重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