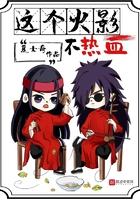笔趣阁>她的字,我的戏 > 微光与尘埃 福利院的午后(第1页)
微光与尘埃 福利院的午后(第1页)
那句“我爱你”说出口后,仿佛有什么无形的枷锁在我们之间悄然碎裂。
回酒店的路上,我们依旧牵着手,但指尖缠绕的力度,眼神交汇时流淌的暖意,都带上了一种全新的、心照不宣的亲昵。空气里弥漫着雨后初霁的清新,也弥漫着一种近乎饱和的甜蜜。
第二天,林夕神神秘秘地告诉我,要带我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是哪里?”我忍不住好奇。
“暂时保密。”她眨眨眼,卖着关子,“不过,需要准备一些小礼物。”
她带着我去了一家很大的文具店和玩具店。看着她认真挑选着彩笔、画本、拼图和各种可爱的毛绒玩具,我隐约猜到了目的地。
“是……去看小朋友吗?”我轻声问,心里有些许忐忑。孩子是纯粹的,但也是敏感的,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应对。
“嗯。”她转过头,对我温柔地笑了笑,“是我一直定期去的一家福利院。那里的孩子们……很特别,也很需要一些陪伴和色彩。”她顿了顿,补充道,“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随时可以离开。”
她的体贴让我安心。我点了点头,也开始学着她的样子,挑选了一些我认为孩子们可能会喜欢的东西——一些颜色鲜艳的贴纸,几本带有漂亮插画的童话书。
车子驶离繁华的市区,开往城郊。最终在一座看起来有些年头,但打扫得十分干净、院子里有彩色滑梯和秋千的建筑前停下。
“阳光之家”——
牌子上的字迹有些褪色,却透着一种朴素的温暖。
我们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走进去,一位面容慈祥、被称为“陈妈妈”的中年女士热情地迎了上来。她显然和林夕很熟络,目光落在我身上时,带着善意的探究和欢迎。
“林小姐来啦!这位是……?”
“陈妈妈,这是苏晴,我的朋友。”林夕介绍道,语气自然。
“苏小姐,欢迎欢迎!”陈妈妈笑着拉住我的手,她的手温暖而粗糙,带着常年劳作的痕迹。
院子里,一些孩子正在护工的看护下玩耍。看到林夕,他们立刻欢呼着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叫着“林夕姐姐!”。
林夕蹲下身,熟练地和他们打招呼,叫着他们的名字,把带来的礼物分发给每个人。她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纯粹而明亮的笑容,像个大孩子。
我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些局促地看着这一切。孩子们拿到礼物时那发自内心的、毫不掩饰的喜悦,感染了我,但那种过于直接和热烈的氛围,又让我本能地想要退缩。
有几个孩子注意到了我,好奇地望过来,眼神清澈,带着询问。
林夕站起身,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孩子们面前,声音温和:“这是苏晴姐姐,她也很喜欢小朋友,今天特意来看你们的。”
孩子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几乎想躲到林夕身后。
就在这时,一个看起来只有四五岁、扎着两个羊角辫、眼睛大大的小女孩,怯生生地走到我面前,仰着头,奶声奶气地问:“姐姐,你也是天使吗?”
我愣住了。
林夕在一旁轻笑出声,低声对我说:“他们有时候叫我天使姐姐。”
我看着小女孩那纯净得不含一丝杂质的眼睛,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仿佛被轻轻触碰了一下。我蹲下身,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僵硬:“我……我不是天使。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姐姐。”
小女孩歪着头,似乎在思考,然后伸出小小的、柔软的手,轻轻碰了碰我带来的那本童话书的封面:“这个……好看。”
我把书递给她:“送给你,好不好?”
她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用力地点点头,抱着书,像得到了什么稀世珍宝,开心地跑开了。
这个小小的互动,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与孩子们之间那扇陌生的门。
其他的孩子见我似乎并不“可怕”,也渐渐围拢过来。他们的问题天真而直接:
“姐姐,你的头发为什么是卷卷的?”
“姐姐,你也像林夕姐姐一样,会在电视里演戏吗?”
“姐姐,你会画画吗?”
我起初还有些笨拙,回答得磕磕绊绊。但在他们纯粹的好奇和善意面前,我的紧张感慢慢消融了。我试着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我不会演戏,但很喜欢看书和写故事。
林夕不知从哪里搬来了画架和一大盒彩笔。她提议大家一起画画。
孩子们欢呼着,各自找了位置,趴在桌子上、甚至直接坐在地上,开始天马行空地涂鸦。
林夕拉着我,也在一个角落坐下。她递给我一支彩笔,眼神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