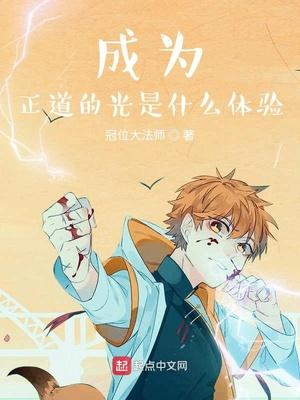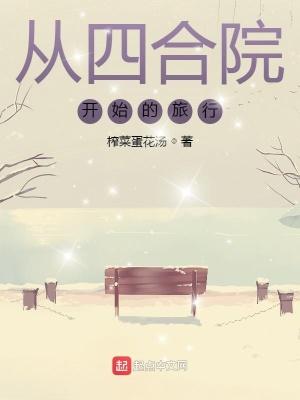笔趣阁>离婚后的我开始转运了 > 第1796章(第2页)
第1796章(第2页)
周婉清的手僵在半空,筷子上的青菜差点掉落。“我可以去吗?”
“当然。”小安笑了,“老师说家长必须到场,不然就不能参加手工比赛。”
那一晚,周婉清回到租住的小屋,整夜未眠。她翻出压箱底的旧相册,一页页擦拭干净,又买了新衣裳,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她甚至开始学用微信,只为能及时回复儿子的消息。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那位快递员终于鼓起勇气,点击播放了那段跨越十二年的母爱遗音。视频监控拍到的画面是:他靠在电动车旁,头盔摘下,双手捧着手机贴在耳边。听到最后一句“就说一声‘妈妈,我过得很好’”时,他仰起脸,任雨水混着泪水滑落,嘴唇颤抖着回应:“妈……我过得很好。我现在有房子,有工作,有人叫我大哥。你放心吧……我一直都想你。”
这段录音被匿名上传至“历史回声”平台,标题为《妈妈,我已经不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小孩了》。评论区很快被点亮:
>“我也想找我妈,可她改嫁后换了号码。”
>“我爸走了二十年,今天我才敢打开录音笔。”
>“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夜里偷偷喊过‘妈妈’。”
阿?将这条录音置顶,并附言:“有些告别本不该发生,但我们仍要相信,重逢永远不晚。”
一个月后的周末,梧桐公园举行首届“声音节”。数百名参与者带着各自的录音笔前来,围坐在草坪上,轮流分享那些藏在心底多年的话语。有人讲述校园霸凌的经历,有人倾诉对逝去亲人的思念,还有一个小女孩怯生生地说:“爸爸,上次你说我考试差就不认我做女儿,但我还是想叫你一声爸爸……你能原谅我吗?”
台下掌声雷动。她的父亲就坐在人群里,红着眼眶站起来,朝她张开双臂。全场静默片刻,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小安也在台上发言。他没有念稿,只是拿着那支旧录音笔,平静地说:“以前我觉得,爱就是天天在一起,谁也不能离开。现在我知道,爱也可以是分开十年后,还能听得见对方的声音。就像这支笔,它不会说话,但它记得所有我没说出口的话。”
台下的周婉清用力擦着眼泪,嘴角却扬着笑。
活动结束时,夕阳西沉,天边染上金紫色的霞光。一群白鸽振翅飞过广场,翅膀划破空气的声音清脆悦耳。阿?站在人群边缘,看着一个个背影离去,有的牵手,有的拥抱,有的只是默默并肩行走。她掏出自己的录音笔,按下录制键:
>“今天,又有三百二十八个声音被听见了。
>有的破碎,有的温柔,有的带着哭腔,有的笑着说谢谢。
>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或许并不缺少爱,
>只是太多人忘了如何开口,或是没人愿意倾听。
>但只要还有人愿意按下‘录音’键,
>就说明希望还在。
>所以,请继续录下去吧。
>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不让任何一个灵魂,独自沉默。”
夜深人静,她回到家,打开邮箱,看到一封来自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函件:经多方评估,“回声计划”被列入全国心理健康教育试点项目,将在三年内推广至百所中小学。附件中还有一份建议书,提议设立“儿童情感表达日”,鼓励家庭开展亲子共录活动。
她合上电脑,走到窗前。月光洒在楼下的小路上,一对母女正牵着手走过,小女孩蹦跳着说:“妈妈,明天我能带录音笔去学校吗?我也想讲故事!”
母亲笑着点头:“当然可以,宝贝。”
阿?转身回到书桌前,翻开日记本,写下一行字:
>“离婚后的我开始转运了。
>不是因为遇到了谁,
>而是因为我终于学会了,
>如何成为一个能承接他人眼泪的人。”
窗外,城市依旧灯火通明。而在无数角落,一支支向日葵录音笔悄然亮起红灯,如同暗夜里悄然绽放的花。